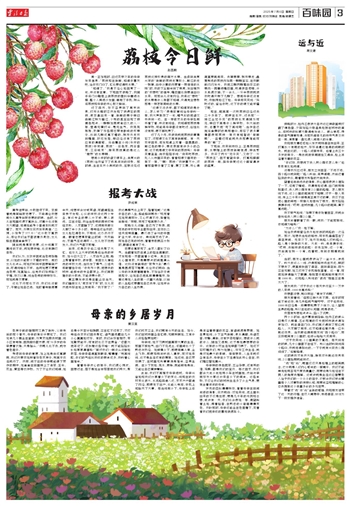赵西蔚
周一正加班时,已过花甲之年的母亲发来信息:“荔枝现在新鲜,知道你喜欢吃,给你放门口了,忙也要记得吃水果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我漫不经心地回复了一句,并没有在意。下班回家很晚了,我随手将门口鞋柜上装荔枝的塑料袋塞进冰箱,整个人窝进沙发里,刷起了手机,转头将荔枝和母亲的关心抛之脑后。
过了四天,好不容易到了周末休息,打开冰箱时忽然发现了被遗忘的荔枝,赶紧拿出来一看,新鲜的果子早已由鲜红转为暗红,个别的甚至出现了棕褐色斑点,一颗颗如同疲惫已久的人一样,显得无精打采,毫无生气。我挑挑拣拣,扔掉了好些腐烂带有酸味的坏果子,找到几颗还算不错的,剥开外皮放到嘴里,软烂发黏,早已经没有了荔枝应有的清甜感。马伯庸在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中写道,荔枝“一日色变,两日香变,三日味变”,原来荔枝真的是这么“脆弱”的水果啊。
想起小学时的语文课本上,肖复兴的《荔枝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那时候,生在北方小县城的我,压根没见过荔枝这种珍贵的南方水果。当读到肖复兴写的“新鲜的荔枝皮薄核小,鲜红的皮一剥掉,白中泛青的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”时,我的下丘脑受到了刺激,发出强烈的“我想吃”的信号,嘴巴里也快要涌出口水来。可那会儿没有网络,我连这“想吃”的水果是什么样都不知道,只得凭空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美味的水果。
“这课文没法学,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,怎么学习?”像是故意说给母亲听一样,我大声抱怨了一句,赌气似的把语文书丢到一边。在一旁做家务的母亲捡起书看了看,并没有说话。我知道那荔枝是稀罕物,可能连母亲都没有吃过,任性也没有用,便不再吭声了。
过了几个月,我很快就把荔枝的事情忘了,对那课文也不再有新鲜感。有一天放学回来,却发现桌上放着一盘圆圆的、鲜红色的果子,果皮表面有许多小的凸起,这不就是课文中写到的荔枝吗?母亲笑意盈盈,向我招招手说:“快来吃荔枝,托人从市里买来的,看看和课文里写的一样不一样。”“啊!荔枝!”我惊喜万分,对着那盘果子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,开心得简直要跳起来。去掉果蒂,剥开果皮,晶莹剔透的荔枝肉如同一颗颗宝石,在我眼前闪闪发光。我把三颗两颗雪白紧实的果肉一同塞进嘴巴里,吃得狼吞虎咽,汁水溅满衣袖,不一会儿,一斤半荔枝就被我吃得只剩下几颗了。想起母亲还没有吃,我惭愧地红了脸。母亲却笑笑说:“妈吃过的,留给你吃,这下你的课文能学懂了吧。”
现在,距离第一次吃荔枝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。即使在北方,过去那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荔枝也变得随处可见,早已不再是什么稀罕物。长大后的我,总喜欢把“完了再说吧”,当作自己拖延偷懒时的常用借口,却忘了很多事情都像那荔枝一样只有短暂的“保鲜期”,一旦错过可能就失去那最难能可贵的“鲜”了。
下班后,我来到市场上,正是荔枝旺季,水果摊上的荔枝新鲜饱满,种类繁多。我买了两斤“妃子笑”,又称了一斤“荔枝王”,回家看望母亲。打算和甜甜的荔枝一起,陪母亲度过这个甜蜜清凉的盛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