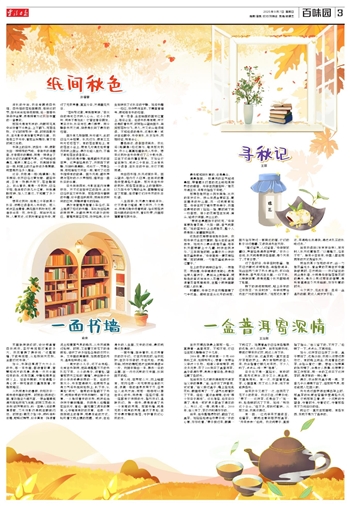王丽
最先感知到秋意的,总是鼻尖。
清晨推窗,一股清冽的空气钻进鼻腔,带着露水打湿的泥土味和某种熟悉的甜香。母亲在院里招呼:“桂花开得正好,来帮我摇些下来吧。”
那棵老桂树在小院东南角,比我的年岁还长。枝头缀满金黄碎玉,藏在墨绿的叶丛里,风一过就簌簌地落。母亲在树下铺开素布单子,我握住最矮的枝丫轻轻一摇,霎时间下起一场香雨。细小的花瓣落在发间、肩头,钻进衣领里,凉丝丝的。
“要赶在晨露刚干时收完,”母亲弯腰拢着花瓣,“太阳一晒,香气就散啦。”她的蓝布衫上沾满桂花,整个人像是刚从蜜罐里捞出来。
收拢的花瓣要细细拣去杂质。我和母亲对坐在竹匾前,指尖在碎金间游走。她说外公最会做桂花酱,每年秋天都要酿上十几罐,封存在阴凉处。“三年困难时期,全靠你外公存的桂花酱换粮食。”母亲捏起一撮花瓣轻嗅,“那时候啊,一勺桂花酱能换半袋红薯干。”
灶上的紫砂锅早已备好。一层桂花一层白糖,母亲铺得极有耐心,像是给婴儿盖被子。最后浇上野蜂蜜,琥珀色的蜜液缓缓渗入花糖之间,甜香混着花香蒸腾起来,在整个厨房里酿成醉人的秋意。
封罐前,母亲忽然往我嘴里塞了勺半成品。甜味在舌尖化开的刹那,窗外恰好掠过一群南迁的雁,它们的影子划过糖罐,又很快消失在天际。
“雁过留声,人过留香。”母亲擦拭罐口,声音轻柔得像在哼歌,“你外公总说,秋天就是要存些香甜,等冬天来了,才有念想。”
过了些时日,母亲启封取酱。桂花已然酿成深琥珀色,凝脂般润泽。她舀出两勺冲了热水递给我,杯口白雾袅袅,香气却沉在水里,一口下去,从喉暖到胃,像是把整个秋天都咽进了肚里。
剩下的装进玻璃瓶,贴上手写的红纸标签:“秋日封存”。母亲说要给远在广州的姐姐寄去,“她那边秋意不浓,来得晚也去得快,得送点扎实的秋味过去。”
后来我读到《东京梦华录》,写开封人秋天收藏桂花:“以糖腌之,经年不坏”。原来千百年来,中国人都在用同样的方式挽留秋天。
而当我某个加班的深夜,舀一勺桂花酱兑水,看金黄的花瓣在杯中重新舒展时,忽然明白——我们留住的何止是秋香,分明是母亲摇落桂花时的晨光,是外公熬过荒年的智慧,是所有值得在冬天来临前,好好珍藏的时光。
今夕何夕,见此秋香。且将一盏温热的甜,敬这人间岁岁不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