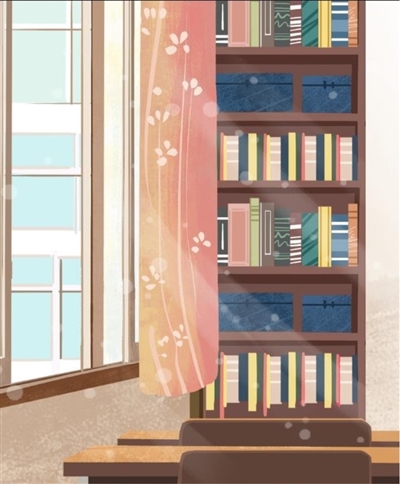张宏宇
书架上又多了几本新书,随意地堆叠在一起,像一堆等待使用的砖块。我常常站在书架前,看着那些还没拆封的书,心里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。这种满足感很奇怪,似乎不是因为读了书,而是因为买了书。
我上学时就爱买书。那时候街上书店很多,几乎每个街角都能看到一两家小书店。橱窗里整齐地摆放着新到的书籍,老板通常坐在柜台后面,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。我最常去的那家书店,老板是个秃顶的中年人,戴着副眼镜。每次我推门进去,他都会从镜框上方瞥我一眼,也不说话,任由我自己在书架间翻找。
那时的书价比现在贵,但买书的乐趣却比现在浓厚得多。我会把一本书拿在手里反复掂量,翻看很久才决定要不要买。买完书回家的路上,总忍不住用手指摩挲着崭新的书皮,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什么时候开始读这本书了。现在不一样了,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滑动,就能把书“加入购物车”,再一划就完成了购买。书的价格便宜得让人吃惊,促销时经常有“满100减50”的活动,算下来一本厚书也就十块钱。我因此养成了“批量买书”的习惯,每次下单至少三五本,多的时候十几本。书到后,拆开包装随便翻看一下,就往书架上塞,那里早就堆满了,新书只能见缝插针地放,或者干脆堆在床头、茶几甚至地板上。
妻子见我买书,总要皱眉:“这些书你都看完了吗?”我支吾道:“慢慢看,总会看完的。”妻子接着说:“上次买的十本才看了一本半,这又买……”我不作声,悄悄把新书塞到书架深处,仿佛这样就能掩饰我的“罪行”。其实我自己也清楚,买书的速度早已超过了看书的速度。书架上的未读书籍已经堆成小山,而我还在不停地往上添。这情形,倒与葛朗台囤积金币有几分相似。只不过他囤的是钱,我囤的是书;他的钱锁在密室里,我的书摆在明处。但本质上,都是囤积癖在作怪。不同的是,世人嘲笑守财奴,却对囤书者颇为宽容,甚至冠以“爱书人”的美名。
夜深人静时,我常常站在书架前,手指轻轻划过那些尚未翻阅的书籍,内心涌起一丝不安。这些书籍,每一本都曾让我心动不已,每一本都在下单时让我满怀期待,然而现在,它们只是静静地立在书架上,积着薄薄的灰尘,等待着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阅读机会。这种感觉,就像我对每一本书都许下了承诺,却又一一食言。
前几天整理书架时,我发现了三年前购买的《荒原》,连塑封都还没拆。记得当时买这本书,是因为读到一位作家的随笔,文中极力推崇艾略特的诗歌。一时兴起,我立刻下单购买,决心要好好研读。但书到后,因为各种原因被搁置,后来又被新买的书籍淹没,渐渐遗忘了。如今再次看到它,塑封已经微微泛黄,而当初的热情早已消退。我拿着这本书,心情复杂,最终还是把它放回了书架,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去读。
我有一位藏书颇丰的朋友,家中藏书多达五千余册。他坦言只读过三分之一,并笑着说:“剩下的等退休后再读。”我心想,退休后他能不能兑现他说的话,还真是未知。但转念一想,我自己不也常对妻子说“这些书留着老了再看”吗?昨天又收到一箱新书,拆封时发现其中一本与家中已有的重复了,这让我意识到,我的购书行为已经超出了实际需求。我买的不是书本身,而是“将来会读这些书”的美好想象;我囤积的也不是知识,而是“精神生活很充实”的心理安慰。
看着书架上满满当当的书,我还是忍不住想继续买。人总得有点爱好吧,我的爱好就是买书,比起打牌喝酒,这已经算是很高雅的爱好了。再说书总是好东西,囤书总比囤别的东西强,我常常这样自我安慰,不知不觉间,我的手已经点开了购书网站的页面。